然而,今年以來,美國和巴西相繼出臺生物燃料相關政策,直接利好兩國本土豆油需求,導致未來大豆壓榨預期大幅提高,而作為大豆壓榨產品之一的豆粕則面臨供應的被動增長,這直接導致國際豆粕價格承壓。恰逢當下中美貿易關系仍不明朗,國內飼料企業擔憂四季度無法重新打開美豆進口渠道而導致壓榨豆源緊缺,而國際豆粕價格下跌卻打開了豆粕進口的利潤空間。
在此背景下,本周國內企業成交了7月裝運的3萬噸阿根廷豆粕,這是自2019年中國批準進口阿根廷豆粕以來首次有記錄的較大數量采購,由此引發的兩個關鍵問題是:1.未來進口豆粕能否常態化;2.若常態化,會給國內壓榨行業與豆粕供需帶來何種影響?
在此背景下,本周國內企業成交了7月裝運的3萬噸阿根廷豆粕,這是自2019年中國批準進口阿根廷豆粕以來首次有記錄的較大數量采購,由此引發的兩個關鍵問題是:1.未來進口豆粕能否常態化;2.若常態化,會給國內壓榨行業與豆粕供需帶來何種影響?
我們首先討論第二個問題。定性來講,若國內全面放開海外豆粕進口渠道,在海內外豆粕價差足夠大的時候,即使國內因為豆源供應緊缺而導致壓榨量減少,也可以通過直接進口豆粕予以補充。這一方面暗示當前國內豆粕價格可能被高估,另一方面也意味著未來國內豆粕定價還將錨向國際豆粕價格。與大豆貿易類似,進口豆粕貿易亦采用基差定價模式,意味著對國內進口商而言,CBOT豆粕未來可能成為另一個定價中樞。
然而,所謂量變才會引起質變,即對于中國年均7000-8000萬噸的豆粕消費而言,只有當進口豆粕數量占比足夠大時,才需要考慮其對于豆粕定價邏輯的重塑。短期而言,需要討論下一年度海外能有多少可供出口至中國的豆粕?
2012年以來,中國年度進口豆粕數量均不超過10萬噸,這意味著此前全球豆粕貿易格局中,巴西和阿根廷的豆粕出口目的地是非中經濟體,暗示下一年度可供出口至中國的豆粕理論最大數量實質是大豆壓榨的最大增量,硬性約束是各國壓榨產能。因此,這一問題等價于明確在巴西與阿根廷名義壓榨產能約束下的最大壓榨增量。
2012年以來,中國年度進口豆粕數量均不超過10萬噸,這意味著此前全球豆粕貿易格局中,巴西和阿根廷的豆粕出口目的地是非中經濟體,暗示下一年度可供出口至中國的豆粕理論最大數量實質是大豆壓榨的最大增量,硬性約束是各國壓榨產能。因此,這一問題等價于明確在巴西與阿根廷名義壓榨產能約束下的最大壓榨增量。
根據USDA報告(Oilseeds and Products Annual),我們大致認為在接近滿開機情況下,巴西2025/26年度壓榨量上限可以達到7000萬噸,較2024/25年度的5700萬噸增長1300萬噸,折豆粕產量約1000萬噸。阿根廷方面,根據羅薩里奧谷物交易所報告(2025.02.28),預計阿根廷2025/26年度壓榨產能將達到6700萬噸。
過去幾年阿根廷大豆產量大致保持在4000-5000萬噸(除2022/23年度),其壓榨產能遠超其產量,使得阿根廷通常尋求巴拉圭大豆進口以提高產能利用率。以保守80%開機率估算(BCR報告稱2024年阿根廷壓榨產能利用率恢復至70%左右),2025/26年度阿根廷大豆壓榨量約5360萬噸,較2023/24年度的4260萬噸增長約1100萬噸,折豆粕產量約880萬噸。綜合來看,巴西與阿根廷在2025/26年度理論最大豆粕供應增量可以達到1900萬噸左右,約占中國豆粕一年消費量的24%-27%,這一比例似乎足以引起國內豆粕定價邏輯的改變。
過去幾年阿根廷大豆產量大致保持在4000-5000萬噸(除2022/23年度),其壓榨產能遠超其產量,使得阿根廷通常尋求巴拉圭大豆進口以提高產能利用率。以保守80%開機率估算(BCR報告稱2024年阿根廷壓榨產能利用率恢復至70%左右),2025/26年度阿根廷大豆壓榨量約5360萬噸,較2023/24年度的4260萬噸增長約1100萬噸,折豆粕產量約880萬噸。綜合來看,巴西與阿根廷在2025/26年度理論最大豆粕供應增量可以達到1900萬噸左右,約占中國豆粕一年消費量的24%-27%,這一比例似乎足以引起國內豆粕定價邏輯的改變。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通常高開機率對應各類維護成本的增加,此外供應增長也會反過來打壓價格,進而抑制開機。因此上述測算僅僅是理論上巴西和阿根廷在下一年度能夠提供豆粕出口增量的最大值。進一步地,如果按照生物柴油的豆油投料增長刺激壓榨來測算,美國大豆壓榨從24.2億蒲左右增至26億蒲左右,提供約500萬噸壓榨增量。
而為了彌補美國、巴西豆油150萬噸左右的出口缺口,極限水平下阿根廷大豆壓榨需要增加700萬噸左右。(但實際增量預計會較估算值偏低,因為缺口可能被其他油脂彌補,且豆粕供應過剩不利于榨利)。綜合來看,南北美合計不到1200萬噸的大豆壓榨增量對應豆粕產量不足1000萬噸,進而影響可能更多體現在短中期,而在年度級別上對國內豆粕供需格局影響相對有限。
而為了彌補美國、巴西豆油150萬噸左右的出口缺口,極限水平下阿根廷大豆壓榨需要增加700萬噸左右。(但實際增量預計會較估算值偏低,因為缺口可能被其他油脂彌補,且豆粕供應過剩不利于榨利)。綜合來看,南北美合計不到1200萬噸的大豆壓榨增量對應豆粕產量不足1000萬噸,進而影響可能更多體現在短中期,而在年度級別上對國內豆粕供需格局影響相對有限。
進一步地,短期若后續國內放開海外豆粕進口渠道,飼料企業可以選擇直接購買相對廉價的南美豆粕,以替代高價南美舊作大豆。這使得四季度中美貿易關系未能改善而引發國內大豆供應短缺的風險得到一定程度緩解,同時豆粕供應預期邊際轉向寬松,進而壓制豆粕價格表現。此外,除非6-8月北美天氣出現較大問題或者中美達成農產品采購協議,否則豆粕也難以從進口原料成本端獲得上行動能。
長期視角下,國內大豆壓榨產能約1.5-1.7億噸/年,而每年大豆壓榨量大約在9500萬至1億噸,產能利用率不足70%。若未來進口海外豆粕成為常態,無疑將對國內壓榨行業形成一定沖擊。此外,國內一年豆油消費量在1700-2000萬噸。若因豆粕大量進口而導致壓榨量萎縮,國內企業需要尋求海外油脂以滿足消費需求(每減少1000萬噸大豆壓榨,將形成約190-200萬噸豆油供應缺口)。
一方面,由于南美豆油、加拿大菜油幾乎沒有可供對華出口份額,因此未來可能會增加采購東南亞棕櫚油用于滿足豆油供應缺口,利好馬棕價格上漲。另一方面,考慮到印尼近幾年在生物燃料領域的加碼,未來國際棕櫚油價格也未必便宜,因此國內亦可能經歷一段高價抑制需求的時期,直到進口利潤重新打開。
一方面,由于南美豆油、加拿大菜油幾乎沒有可供對華出口份額,因此未來可能會增加采購東南亞棕櫚油用于滿足豆油供應缺口,利好馬棕價格上漲。另一方面,考慮到印尼近幾年在生物燃料領域的加碼,未來國際棕櫚油價格也未必便宜,因此國內亦可能經歷一段高價抑制需求的時期,直到進口利潤重新打開。
在利潤分配上,以往油廠進口大豆并進行壓榨,貿易商向油廠采購豆油和豆粕,然后銷售至下游企業,形成“上游油廠掌握壓榨利潤-中游貿易商‘賺取差價’-下游消費企業‘被動接受報價’”的利潤分配格局。若未來海外豆粕進口常態化,對油廠而言,由于壓榨量萎縮,可能導致其營業收入下降;
對貿易商而言,各國生物燃料政策的推進導致全球油脂價格上行以及更高的關稅稅率(9%)暗示油脂進口成本將高于以往向油廠采購的成本,盡管成本抬高的部分可以向終端企業轉嫁,但貿易商仍需要承擔一部分;對下游飼料企業而言,其可以繞過油廠,直接進口海外相對廉價的豆粕,成本有望下降。綜合來看,在這場潛在貿易格局的轉變中,油廠和貿易商可能會遭受一定損失,而下游企業則有望在成本端獲益。
對貿易商而言,各國生物燃料政策的推進導致全球油脂價格上行以及更高的關稅稅率(9%)暗示油脂進口成本將高于以往向油廠采購的成本,盡管成本抬高的部分可以向終端企業轉嫁,但貿易商仍需要承擔一部分;對下游飼料企業而言,其可以繞過油廠,直接進口海外相對廉價的豆粕,成本有望下降。綜合來看,在這場潛在貿易格局的轉變中,油廠和貿易商可能會遭受一定損失,而下游企業則有望在成本端獲益。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分析均建立在國內政策允許海外豆粕規模化進口的前提下,即第一個關鍵問題。根據海關總署,截至6月27日,目前阿根廷(14家)和巴西(289家)有部分企業已經通過境外動植物及其產品檢疫注冊登記,即允許向中國出口豆粕。同時根據不完全統計,僅在上海海關進行進出口飼料經營備案的企業至少有457家,即允許從海外進口豆粕。簡言之,目前國內企業已經具備從海外進口豆粕的可能性。
除此以外,與進口大豆類似,國內企業進口豆粕需要持有重要的“三證”:商務部核發的自動進口許可證、海關總署核發的進境動植物檢疫許可證以及農業農村部核發的轉基因(GMO)進口安全證書。三項證書中,較難申請的是GMO證書,過往時常有部分進口大豆因為不滿足標準而無法獲得GMO證書,進而不能通關到港。
正如前文所述,若未來國內企業進口海外豆粕常態化,或將導致國內壓榨產能閑置率升高,不利于大豆壓榨產業良性發展。因此不排除國家可能會在政策上限制海外豆粕規模化進口,例如嚴格限制GMO證書的發放,使得豆粕進口成為“空中樓閣”,進而國內豆粕定價仍然錨向CBOT大豆。因此,國內進口豆粕能否常態化也是后續討論的關鍵議題。
正如前文所述,若未來國內企業進口海外豆粕常態化,或將導致國內壓榨產能閑置率升高,不利于大豆壓榨產業良性發展。因此不排除國家可能會在政策上限制海外豆粕規模化進口,例如嚴格限制GMO證書的發放,使得豆粕進口成為“空中樓閣”,進而國內豆粕定價仍然錨向CBOT大豆。因此,國內進口豆粕能否常態化也是后續討論的關鍵議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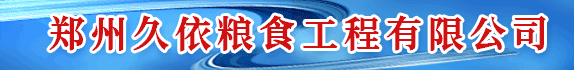







 ??魯公網安備 37140202000174號
??魯公網安備 37140202000174號